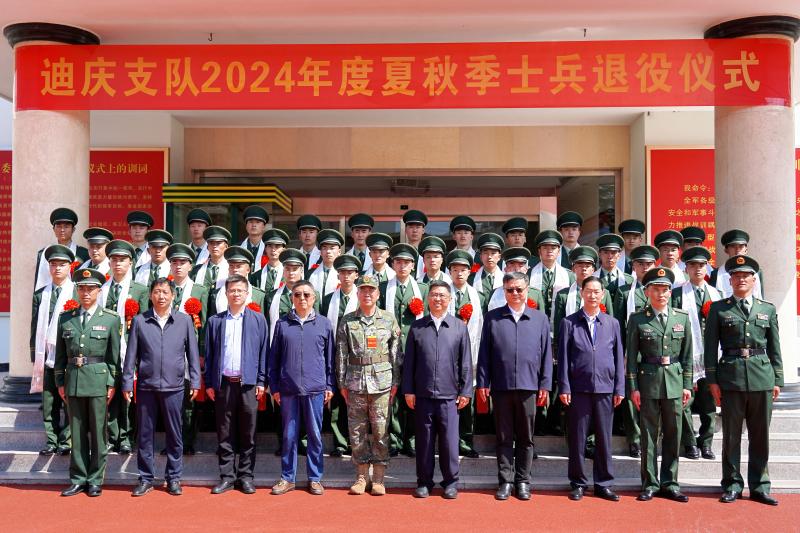|
她是一株柳,柔美、空靈而干凈。她年齡不大,每個枝條都很光滑,枝條上綴滿綠色的葉子,翠綠翠綠。 在一片草坪邊,她一年年長大,每天都看著人來來往往。有在她腳下休憩的,有甜蜜的情侶靠著她擁吻的,也有一些放風(fēng)箏的人群。她有時也會嘲笑放風(fēng)箏的人,風(fēng)箏總會斷線飛走,那時只能手握斷線看著空中飛走的風(fēng)箏徒留一絲嘆息,可是人們就總喜歡玩這樣的游戲。在她心中,這些人都有一點(diǎn)幼稚。 然而有一天,她的視線里多了一個風(fēng)箏,有著絢爛的花朵,在她周圍慢慢地飛旋。他的絢爛驚動了她,這是怎樣的一只風(fēng)箏?有著堅硬的箏骨,卻滿身的花哨,怎么形容?嗯,就像妖精,妖精一直以來就是形容女子的,可他分明就是一個妖精。看他在風(fēng)中飛舞的樣子,比女子都嫵媚。他好像感覺到她的注視,回頭笑笑,對她眨眨眼。 慢慢地熟絡(luò)起來,他們之間變得微妙。她開始期待他的出現(xiàn),絢爛著她的視線。渴望、期待又抗拒,而最讓她膽戰(zhàn)心驚的是她在暗暗設(shè)計很多種勾搭他的方式,但是每一種幻想很快被自己否定。而且好像根本就沒必要設(shè)計勾搭,因?yàn)樗麄冎g已經(jīng)默契到了一個眼神或者動作,對方就能了然彼此的心境。 他開始在風(fēng)中說一些甜膩的話語,她不明白他的語言怎么就那么豐富?每次都會給她驚喜都會讓她悸動。 他甚至在風(fēng)中拾到一朵蒲公英,都借著風(fēng)勢,插到她的發(fā)上。他的手指修長而柔軟,輕輕地?fù)崦凉饷艿拈L發(fā),然后旁若無人地親吻著她。他說她是他的全世界,是他的唯一。她一次次醉倒,這樣的愛戀,在她的夢中曾出現(xiàn)過千萬次。 她不明白,她是一株柳,他是一個風(fēng)箏,兩個世界的人怎么可以相愛?可是事實(shí)是,他們真的愛了。 有時愛情就是這樣,沒有什么可能或者不可能。 如果說,他沒出現(xiàn)之前,她的生活是一洼平靜的湖水,平淡卻寧靜;那么他來到她的世界中,她的生活則是有激流險灘的一條河,時時波濤洶涌。 她很滿足于這樣的改變,每天金燦燦的陽光照射在她濃密的發(fā)上,有露珠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她伸展著滿身的葉片,在陽光中微笑,所有的細(xì)胞都唱著歡樂的歌曲。在風(fēng)中,她也開始搖擺出各種嫵媚的姿態(tài)。 細(xì)雨蒙蒙,沒有他的日子,她就仰起頭,沖洗著自己的秀發(fā)。雨后的她變得更秀美,然后期待著他的出現(xiàn)。 然而,他時有時無。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yùn),他被一根細(xì)細(xì)的繩緊緊地牽著,放遠(yuǎn)了拉回來,拉回來又放出去。很多次她看見他飛得很高很高,以翱翔的姿勢,她看見了她眼中很多的渴望,他想飛得更高,可是每次都會被拉回去。 只要他來的日子,她就覺得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如果一直都是這樣子,多好。可是一切都在一個黃昏后破滅了。 那天,夕陽的光暈溫柔地鋪射在他們身上,多么美好的一個寧靜的傍晚。他飛著,嫵媚地?fù)u擺著,對她含情地笑著。她心里有溢出水的幸福,然而卻也有隱隱的不安,她不知道她的不安源自何處,他不是在她的視線之處嗎?他不是依然對她說著像蜜一樣甜的情話嗎?可是她的心卻很慌,就像一鍋開水,嘩嘩地響著。然后她聽到“咚”的一聲響,很輕卻震得她心疼。然后就看到放風(fēng)箏的人拼命追趕著,然后看到他回頭看了一眼,就慢慢地消失在她視線…… 放風(fēng)箏的女孩子坐在她腳邊,賭氣地摸出包里的一面小鏡子,狠命的甩向旁邊的一塊石頭。她看到上百張悲傷悸動的臉在地上閃爍,分不清是女孩子的還是她的。 一切又好像什么都沒有發(fā)生,太陽依舊升起,雨照樣在下,而她卻已經(jīng)不是以前的那棵柳。這個城市沒有了他,變得寂寞和蒼白。 夜寂靜得像一片荒涼的沙漠。而她的心則比沙漠更荒涼。她再也無法安靜地入睡,滿腦子都是有關(guān)他的一切。在安靜中,她想起了他的種種,好像也不是那么完美,好像有點(diǎn)輕佻,也經(jīng)常對身旁的風(fēng)箏調(diào)調(diào)情,說過一些地老天荒的話語。他不是那么好,真的,甚至不算好。有諸多的缺點(diǎn),可是想完了他所有的不好,他依然還在她的腦海里,日甚一日。 生活缺少了他,再怎么絢爛的風(fēng)景也入不了她的眼,在黑夜中,每夜每夜她的腦海中都是他一切,他在她心目中依然是帥得要命的那一個,獨(dú)一無二的那一個。其實(shí)一開始她就知道他只是一只風(fēng)箏,總會有飛走的時候,可是沒想到他飛走了,她的世界卻如此地沉靜下來。 她的眼睛里儲滿了濃得化不開的憂傷,反復(fù)輕輕一碰就會有水滴溢出。她試過很多很多種讓自己快樂起來的方法,她在寧靜中聽著風(fēng)的低語輕唱,她學(xué)飛鳥的歌聲,她在風(fēng)中嫵媚地舞蹈著,她甚至企圖回到以前那種平靜的生活,可是再也回不去。她的心境再也無法平靜,她的心時常感覺像一鍋被煮沸過了的水,冷卻下來后還經(jīng)常聽見那嘩嘩的聲音。她看著放風(fēng)箏的人快樂地飛奔著,她都會有疼痛的感覺。 心,一天天空了。她想找東西拼命填滿,可是就像一個沙漏,總有沙不斷地流失。一開始就知道結(jié)局,你怎么能奢望一只風(fēng)箏天長地久的愛戀?可是自己還是變成了那只撲向火的飛蛾。 一天又一天,她瘦成了一縷魂魄的樣子。連深深扎入土里的根都漸漸松動。 綠綠的發(fā)絲漸漸沒了水分,慢慢黃了。意識漸漸渙散,她感覺自己也變成了一只風(fēng)箏,騰空飛舞。 在飛舞中,她對那只早已經(jīng)飛遠(yuǎn)的風(fēng)箏說:“請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對自己殘酷。”(那麗珍) |
主頁 >香格里拉網(wǎng) > 迪慶文藝 > 正文
飛遠(yuǎn)的風(fēng)箏
來源:香格里拉網(wǎng) 作者: 發(fā)布時間:2011-11-14 10:39:21

頻道精選
- 2024 年迪慶州新聞系列綜合高級職稱定向評審?fù)ㄟ^人員名單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qū)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dá)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qū)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dá)美景2024-09-05
- 張衛(wèi)東到迪慶交通運(yùn)輸集團(tuán)公司開展調(diào)研2024-09-05
- 福彩代銷者:增強(qiáng)責(zé)任意識 倡導(dǎo)理性購彩2024-09-04
- 中央專項(xiàng)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xiàng)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xiàng)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慶人,這場活動需要您的參與!2024-09-04
- 積極參與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慶見義勇為”宣傳募捐活動倡議書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