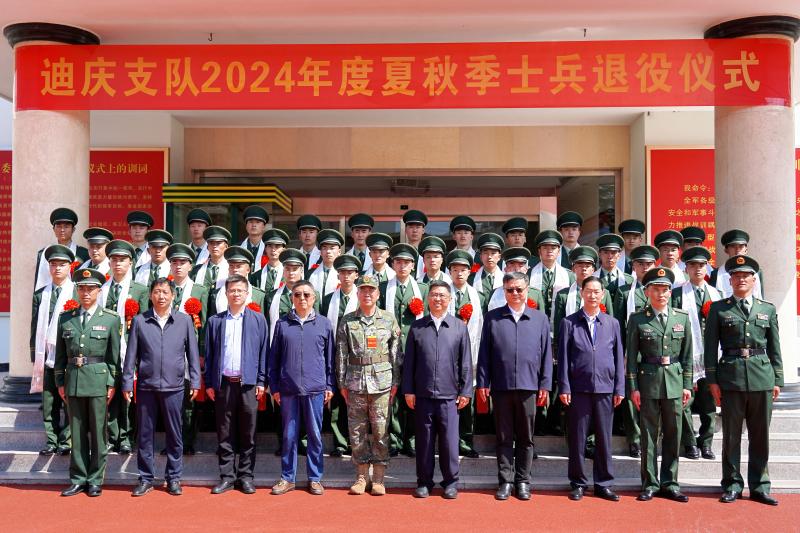|
這個故事是我在山西當兵時,女兵玲探親時對我講的。記得那應該是一個天氣晴好的秋日下午,玲坐在我辦公桌的對面,耀眼的陽光斜射進來,照在玲紅潤的臉龐上,格外地迷人。玲知道我搞寫作,就一再懇求我幫她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她說如果能這樣,就當她對死去的強表達感傷和懷念吧。 周遭一片寂靜。坐在玲對面,我開始傾聽她講述那段令人垂淚的故事。玲是山西人,1990年12月入伍到了西藏。惡劣而兇險的環境,讓玲領略了當女兵的美麗和壯烈,也感受了太多關于兵們在雪域高原攜著死亡奔跑,在冰封的河流中搏擊生命極限的情景。玲說,那時候她在西藏的一所部隊的醫院里當護士。由于環境的惡劣,她所在的醫院每天都要接納不少因高寒缺氧而危及生命的病人。故事也就從那時候開始了。 有一天,玲正在給一位病人換藥,忽然聽到背后有人喊了一聲“姐”。扭頭一看,是一名面容清癯但很英俊的小戰士。玲發現再無旁人,就當幻聽,只本能地笑笑算作招呼。 “姐,”這位小戰士這樣喊著玲,突然抓住了她的手。憑著力量的感覺,女性自衛的本能使玲第一反應便是將手抽出來。然而,小戰士卻緊緊鉗住不放,兩眼死死盯住玲,“讓我看看你,讓我好好看看你!讓我喊你姐吧。” “你滾開,神經病!”為了面子,玲將聲音壓低從牙縫里濃縮成炮彈,兩眼凝煉成兩束帶火的利劍,狠狠向他刺去。小戰士果然不堪一擊,連忙松開玲,眼里含著深深的傷痛,喃喃自語。而玲卻像一只驚恐的鹿兒落荒而逃,只聽見身后有一句“我不是那個意思……” 玲大獲全勝卻淚流不止。見鬼!神經病!瘋子,玲一次次在心里詛咒這個“冒失”的小戰士。 “喂,你的電話。”幾天之后,同事喊玲去接電話,玲從椅子上彈了起來。 “喂!” 一陣短暫的沉默后,傳來一個極低沉的聲音:“是你嗎?” “嗯,你是誰?” “你一定在記恨我吧?其實你聽我解釋……” 不象話,成何體統,小戰士竟然查到了玲的電話號碼。 “你聽著,神經病,請你自重,我不想聽你的解釋!”玲氣極敗壞地將電話掛斷。 幾天來,玲的情緒壞到了極點,小戰士在玲心中的陰影無法抹去。然而更讓玲忍無可忍的是小戰士竟然會找到玲的宿舍來。 那天,玲正讀一部叫作《雪域軍魂》的書,小戰士突然推門而入。氣極的玲,頓感脖子僵硬,渾身發抖,冰涼的雙手捏成瘦小的拳頭,迅速將門后的拖把、桌子上的墨水瓶、水杯收集眼底,心里反而坦然了許多。 沉默、僵持,此時,玲竟還能想起“誰堅持到最后誰是強者”這句話。 “你弄錯了。”小戰士終于僵持不下去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玲臉如青鐵。 “不!我不想干什么,真的,我只求你聽我把話講完。”小戰士近乎哀求。 “那天,我是辦了一件愚蠢透頂的傻事。可我確實沒有別的意思。僅僅是想看看你……因為你長得太像一個人,我唯一的姐姐……她死于車禍,是在一個陰雨連綿的秋天。見到你,我簡直不敢相信,世上真的會有長得這么相似的人嗎?我甚至想到讓我年邁多病的父母也來看看你,僅僅是想看看你,真的,僅此而已……請原諒。”說完大顆大顆的淚珠從小戰士的臉上滾落下來,砸在地上,很響。 啊!聽了小戰士的話,不堪一擊的竟然是玲,她一下癱坐在椅子上。這些天自己干了些什么呀,竟然不斷地給這顆受傷滴血的心上撒鹽。此時,玲的淚水也不爭氣地在這個她詛咒、憎惡過的小戰士面前流了出來。 “如果說小戰士說明事情的真相,就意味著故事結束的話,那未免又有點太簡單了。問題是后來……”玲說著,眼淚就涌了出來。 “后來怎么啦?”我迫不急待地問玲。 玲哽咽著聲音繼續講下去。在小戰士離開玲之后,玲很快就知道他叫強。是山西人,和自己是老鄉。強從小向往軍營,為了當兵,他瞞著父母瞞了年齡報名參軍到了西藏。入伍那年,他才滿16歲。在西藏,強選擇了一個最為艱苦的哨所。在與雪山為伍的日子里,他生命之中的每天幾乎都需要一次次地經歷著缺氧短氣所帶來的恐懼和威脅。但無論怎樣艱苦,強始終讓一種樂觀的精神貫穿他的一言一行。他挺住了,他把自己寶貴的青春獻給了雪域。然而,就在他服役期滿即將脫下軍裝時,他被檢查得了白血病,且已近晚期。在生命進入倒計時的日子里,強沒有放棄對生命的渴望,他依然用雪域高原上鑄就的那種樂觀和豁達去感召身邊的每一個人。后來,強終于微笑著離開他的哨所和戰友們,永遠長眠在那雪域高原。但是,彌留之際,他仍然十分思念他故去的姐姐,就托一位戰友找到了玲,并把一條鮮艷的紅紗巾送給了玲。那位戰友捎話給玲,強說玲長得像他姐姐,他姐姐生前最愛系一條紅紗巾…… 玲這樣說著,便從懷里掏出了那條紅紗巾,用手一遍一遍地摩挲著,晶瑩的淚水又一次奪眶而下。 后來,為了追尋愛情,我調離山西,到了南方。再后來,我聽說本來要提干的玲也離開了西藏的部隊,復員回到了山西。回來不久,玲很快就結了婚,并把強的父母接到她那里。多年以后,當我問起玲為什么這樣做時,玲說不為什么,只為強留下的條紅紗巾,一條永遠的紅紗巾。(劉建忠) |
永遠的紅紗巾
來源:香格里拉網 作者: 發布時間:2013-07-11 09:46:52

頻道精選
- 2024 年迪慶州新聞系列綜合高級職稱定向評審通過人員名單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張衛東到迪慶交通運輸集團公司開展調研2024-09-05
- 福彩代銷者:增強責任意識 倡導理性購彩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慶人,這場活動需要您的參與!2024-09-04
- 積極參與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慶見義勇為”宣傳募捐活動倡議書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