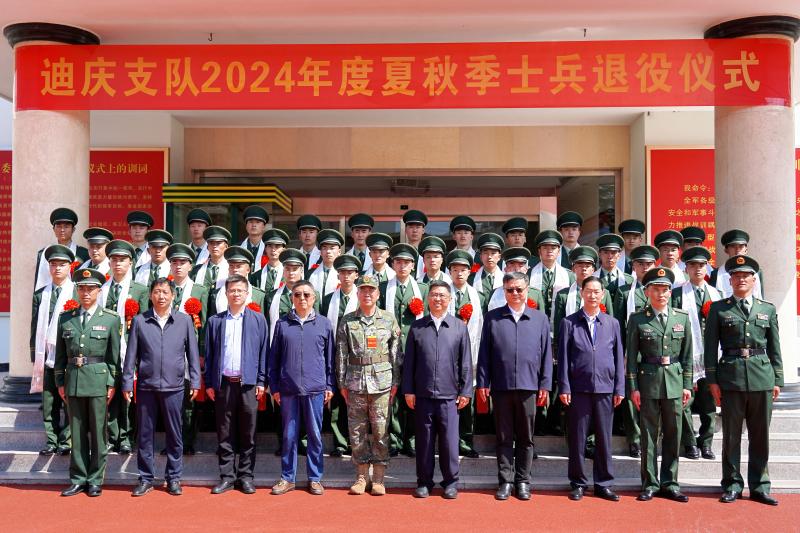|
某天看黎小桃的文章,里邊有一句:“劉邦出生時身邊盤著一條蟒蛇,黎小桃出生時身邊盤著一位醫生。”俺當年出生時身邊非但盤著一位赤腳醫生,還出現另一異象——額前的頭發蓋過眉毛。可能該赤腳醫生久經“沙場”,還從未見過一出生頭發就這么長的。 我本人對頭發最早的記憶,是母親將我的頭發高高綰起,扎成一束馬尾。林沖遭發配到野豬林那場戲,他的發型就很像我這個。接著我還被戴上一只發卡,發卡上頂著一團用紗巾扎的大紅花。這種打扮是從畫上學來的,名曰“祖國的花朵”。而后母親帶我去做客,接受同桌吃飯的人的贊美。 那個年代的電影里,只有女特務、太太、小姐之類才燙發。好女人的頭發,基本上是從正中分開(或者三七開),用兩個夾子朝兩邊夾住,發梢在耳后齊刷刷地翹起;要么就是雙辮子或獨辮子。在這種思潮下,我小小的心靈還是悄悄地認為,太太小姐的打扮確實比婦女主任、村姑好看。我們小孩子玩演戲,要是我被分配演太太小姐,我就假意繃著臉,做出不情愿演反派的樣子,其實心里挺樂意的。正所謂,在主旋律和美之間,俺寧可選擇美。 后來社會進步到了連正派人物也可以燙發的地步。只是我們那地方作為小鎮,還沒有哪位婦女敢開風氣之先河,勇敢地燙一頭卷發。在此種時代背景下,母親大概想在我的頭上實現她的愿望,用燒燙的火鉗為我燙了一回。焦糊味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彌漫到今天。當時我肯定很難看。之后母親去大理市(那時叫下關)做客。母親聰明,在一家理發店門口觀摩了一下,就掌握了“冷燙”的要領,回來時就買了一瓶冷燙精,按那上面的說明為我燙發。父親很重視這事,蹲在一邊看。過了兩個時辰,我頂著一頭羊毛般的卷發出去玩,就感覺自己同以往不一樣、同別的小孩不一樣。這直接導致我變“驕傲”了。與父親單位對門那家小男孩玩的時候,我突然無端地對他說:“不和你玩了!”他大哭,嘴巴張得很大,連扁桃體都露出來了。以后我就常常收拾他:玩到一半,突然就宣布不跟他玩了。每次他必哭得展現扁桃體。去年我回老家過春節,遠遠看見一個半禿的中年胖子,雙手插在褲袋里看舞龍。想起他童年的扁桃體,不禁莞爾。 我也像母親一樣喜歡為別人梳頭。我常坐在門檻上或者田埂上,為小伙伴弄頭發,條件是我的頭發也必須讓她弄。有段時間姨媽帶著她女兒雪梅回娘家來,雪梅長著一頭長發。我可高興了,一會兒幫她梳《白毛女》中的喜兒式;一會兒又把她所有頭發梳到頭頂正中,編兩根沖天的辮子,而后將辮子對折成角狀,此乃“仙女式”。雪梅說她想梳“黃蓉式”,于是我在仙女式的基礎上,將她左右鬢邊各留出一撮頭發,編成極細的辮子垂到胸前。 俺長大以后,美容美發界突然繁榮,盛況空前。這一定是改革開放的功勞。在我們那個小鎮,大街上發廊此起彼伏,這兒剛剛倒閉轉讓,那兒又擇吉日開張。我見過一小理發店,采取大發廊的經營模式,店長、燙染師、造型師,這樣那樣的師一應俱全,每天早晨由一位領頭的肩扛大旗,大家排成一串,沿著大街一邊跑一邊呼口號。我還見過一理發店,取名為“大公牛形象公社”,使人聯想到生產隊飼養耕牛,用于犁田。我見到一個小伙子,竟把一頭亂發染成草綠色,像戴了頂綠帽子。我還見到一個女的,頂著個黃發紛披的大腦袋,活像雄獅。人們的想法是越來越怪異了。直頭發的要燙卷,天生卷發的要搞“負離子拉直”。就連我這自詡有主見、從不趕時髦的人,也時而將發梢燙朝外卷,弄成“翻翹式”;時而將頭發從根部一直燙到稍部,據理發匠說這叫“波斯頭”。我可憐的頭發被折騰得發黃、發脆且尖端開叉,風一吹就張牙舞爪呈爆炸狀,只要遇上一粒火種,就極有可能造成燎原之勢。我思念我那黑而且直的天然長發。決心要找回我的頭發。 孩子入學以后,我每天呆在福貢一中那個著名的破值班室里讀書做學問,并開始蓄長發。由于前些年被孩子給磨得喪了志,現在又開始讀書,難免思維亂竄、意念飄浮,這情狀好比見了新發型就按捺不住;漸漸地有了閱讀的感覺了,雖不再抓耳撓腮如坐針氈,但還未養成習慣,稍不注意就可能半途而廢,這又如同蓄發蓄到不長不短之時最容易產生剪掉的念頭。 如此堅持很久,俺終于基本上克服了惰性,使心境歸于平和,并得出一個巨大的道理:原來蓄發與養性很有關系。長發非一日能留,需要養護,需要像提升智慧與情操那樣長期堅持積累。而性情浮躁之人的注意力,往往徘徊于時尚潮流之間東張西望見異思遷,根本就沒法耐下心來鍥而不舍地蓄一頭長發。 雖不能說留長發的女人就一定有恒久的毅力和耐心,但至少可以說,若非民俗或社會風氣使然,能夠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抵住時尚潮流之誘惑蓄一條長辮子的女人,她的心性一定較為專一、安定、平和,她一定可以靜下心來做一點事情。 寫到此,俺突發奇想,覺得美容美發界應該在經營中考慮加入形而上的內容。哪家美發店要是有本事讓顧客的心智與頭發一道受到養護、一道成長,那才叫成功。(作者:馬瑞翎) |
頭發
來源:香格里拉網 作者: 發布時間:2015-03-09 09:49:08

頻道精選
- 2024 年迪慶州新聞系列綜合高級職稱定向評審通過人員名單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張衛東到迪慶交通運輸集團公司開展調研2024-09-05
- 福彩代銷者:增強責任意識 倡導理性購彩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慶人,這場活動需要您的參與!2024-09-04
- 積極參與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慶見義勇為”宣傳募捐活動倡議書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