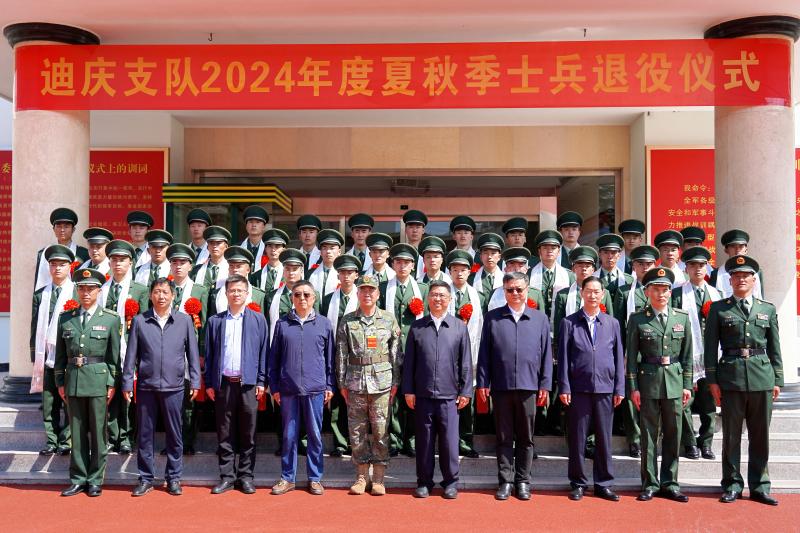|
(三)打場憶事 自我記事起,村里就有兩個打場,一個在山腳下村民相對集中的山坡上,另一個在我家的山背后,我們村的小學和養豬場就在打場旁邊。 離我家最近的打場是村里的文化活動中心和村民的勞作中心,放露天電影,村民開會、學習都在這里。這里也是我們童年時最喜歡的一個地方,除了讀書,我們還會在這里玩耍,跳皮筋、跳繩、踢毽子或者在打場上方的亂石倉用石頭砌一小段石墻,找來樹枝和櫟樹葉做房頂,建一個自己的小天地。 據母親說,我一歲多剛會走路、說話時,大姐正在讀小學,家里沒有人照顧我,就讓大姐把我帶到學校。那時,和大姐一樣,不少學生除了讀書,還得帶弟弟妹妹。有的學生把不會走路的弟弟妹妹背在背上帶到教室里讀書,小孩餓了還要背到母親勞作的地方喂奶。 大姐的同桌也把她家五歲的妹妹小老六帶來學校照管。小老六說話含糊不清,我和她接觸多了,不久后說話也和她一樣。母親被嚇了一跳,之后一段時間,無論多忙,她都把我帶在身邊,不允許我到學校去玩,直到我講話時大部分發音糾正過來。 我八歲時要上小學了,母親給我縫了一個好看的花書包。上學第一天,我在教室里看見了小老六,老師安排我們倆成了同桌。她一見到我就開心地叫著我的乳名:“阿順,來,坐。”并把板凳讓給我一大半。小老六雖然比我大,但因為聽力不好,升學考試不及格,一直讀一年級。 村里的小學只有一間教室,一到三年級的學生都在一起上課。老師先給三年級的學生授課,然后是二年級,最后是一年級。到我升到6公里外的高小讀四年級時,小老六輟學回家參加勞動去了。在后來的7年時間里,我一直在外讀書,和她幾乎沒有見過面。后來,聽說小老六精神失常了,經常會打人,但她始終記得我,常常會跑到我家屋后,看我有沒有在家,拉著母親找我。 有一年放暑假,我看到小老六就坐在我家屋后的一塊大石頭上。當我從她身邊經過和她打招呼時,她問我有沒有見到阿順。我的心里忽然酸楚起來。她只記得那個跟著她咬著舌頭講話的小女孩,至于長大的我,已經不是當初那個跟她無話不談的玩伴了。 打場上曾經辦了一間集體食堂,村民在這里統一吃大鍋飯,大家都把這里叫做伙食堂,這個稱呼一直沿用到現在。伙食堂有一個寬闊的打場,四周矗立著高高的麥架,每到莊稼收獲的季節,村民就把莊稼人背馬馱地運到打場上。小滿前后收來的是豌豆、蠶豆、小麥、青稞,寒露前后收來的是玉米、大豆、四季豆。村民把豌豆、蠶豆、小麥、青稞和大豆一捆一捆地架到麥架上晾曬,把玉米像小山一樣地堆在打場上。吃過晚飯后,村民背上籃子,圍坐在玉米堆四周,燒起一盆松明子火,開始剝玉米皮。剝的時候需要左右手充分配合,左手握緊玉米,在右手的中指上栓一個一頭尖利另一頭圓鈍的簽子,用簽子尖利的一頭刺開玉米殼的頂部,使勁一撕,金黃的玉米就露出來了,除了需要留幾絲玉米皮用來捆扎架到麥架上晾曬外,其余的都可以撕掉。那些沒有皮的玉米棒子就直接堆在曬樓上。 大人們都苦中作樂,一邊剝一邊講笑話,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給村里的男孩說媳婦,給女孩找婆家,相互打親家。小孩子們半懂不懂,有的被逗哭了、有的順著大人的意思叫婆婆、岳母,不管什么結局,大人們都會開心地笑。 有時候只要有人起頭,他們也會樂此不疲地對唱山歌。 故鄉的山歌大多是填詞即興創作的,這邊唱那邊和,有時候是男女對唱,有時候是一個人唱其他人和。很多時候白天掰來的玉米皮剝完了,山歌還沒有唱完,唱的人和聽的人都意猶未盡。大家稱完自己剝出來的玉米,記好工分后,依依不舍地回家了。 等到打糧食的時候,打場上又是一番熱鬧的景象。 需要大規模打糧食的時候,村里就會派手巧心細的村民修整打糧場。那時候,村里沒有水泥,修補打糧場的用材就是山里的黃泥。修整時要把黃泥篩細,除去泥里的石頭,和上水攪拌均勻后鋪平在事先灑過水的潮潤的糧場上面,等水汽蒸發一部分時就用木錘不斷敲打,直到糧場的地皮又平整又堅硬。 打麥子、蠶豆、豌豆、稻子等作物時,社員們分工合作,有的爬在麥架上取下麥把子,有的將麥把子鋪平在打場上。曬好一場后,男人們便開始揮動著手中的糧桿使勁地打。 糧桿是打糧的一種常用工具,一截較短的金竹作為母桿,一根較長標直的山楂樹枝作為子桿,母子桿之間由一根麻皮搓成并在灶灰水里煮過的細麻繩拴在一起。打糧時,手握住母桿,用子桿反復捶打麥穗或者豆莢,麥粒或豆粒就被打出來了。 打糧場上往往10人或者8人組成一組,兩邊人數相等,對著打。團體協作打糧時,大家都形成了一種默契,子桿緊挨自己的身體,統一左打一次、右達一次,一直重復。打糧前,為保證大家的安全,每個人都會細心地檢查母子桿之間是否栓牢實,麻繩是否有破損。等到麥粒基本打出來后,兩個糧桿用得嫻熟的年輕社員就會圍著打場翻打麥草或豆草,徹底將包裹在里面的糧食都打出來。這時,大部分人都靠邊休息,翻打的人就像是打麥場上的舞者,憑借著矯健的身影和灑脫的翻打贏得大家的陣陣掌聲。 男人們打完一場,該女人們上場了。頭戴五顏六色圍巾的婦女用糧叉將打好的糧草從打場挑到旁邊的空地上,之后她們有的用大竹篩篩去粗糠,有的在打場的風口上安裝好大簸箕,站成一排,舉著小簸箕依靠山風的力量將糧食中的雜物吹走。風大的時候,小簸箕里和著糠的糧食像水流似的流下來,糧糠像飛舞的雪花翩躚著離開簸箕,遠遠望去就像一條條瀑布在流淌。沒風的時候,她們就把小簸箕放下來,穩在腰間歇息,一起嘬著嘴噓噓地喚風,沒一會兒,真的就有一陣陣山風吹來,“瀑布”又開始流淌了。 打糧的日子,小孩們也是快樂的。我們用手搓麥稈的一頭,讓麥稈尖分開形成一個傘狀,在中間放一顆豌豆,仰起頭,把麥稈豎起來一吹,豌豆就在麥稈上轉動著跳舞。我們的樂趣就是比誰的豌豆跳的時間最長。很多時候,我們都在尋找廢舊的瓦片,小心地修理成瓦子,或者撿拾白色的“馬牙石”敲打成大小均勻的石子,坐在打場平整的地上比賽抓石子。 等到大人們把架在麥架上的黃豆、小麥下完后,我們就開始比賽爬麥架,或者用麥架最下面較細的木桿作為單杠,在上面正翻反翻。 打麥子的時候,我們就鉆進麥草堆里玩捉迷藏。剝玉米皮的夜晚,我們則躺在玉米堆里睡覺,直到大人剝完玉米皮準備回家了才醒來…… 包產到戶后,集體化整為零,再加上后來村里的學校撤并,打場一度陷入蕭條。沒有了玩耍的小孩,也沒有閑聊的老人,更不見剝玉米皮的村民的身影。當時,有人想把打場和學校的操場挖開種莊稼,最終在父親等人的阻止下保留了下來。后來村里建村民活動場所,打場上建起了兩棟平頂房作為黨支部活動和學習陣地,中間留了一個籃球場,地面做了水泥硬化。每逢村民集中起來跳葫蘆笙、過節或者開會時,打場上又會短暫地熱鬧一番,舉行文藝演出、籃球比賽時,村民從曲曲彎彎的山路上走來,聚集在一起,坐在籃球場四周觀看或者閑聊,打場上的笑聲又在小山村里回響。 (未完待續) |
故鄉的原風景
來源:香格里拉網 作者: 程志開 發布時間:2021-08-31 09:57:03
上一篇:哈 巴 西 坡

頻道精選
- 2024 年迪慶州新聞系列綜合高級職稱定向評審通過人員名單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張衛東到迪慶交通運輸集團公司開展調研2024-09-05
- 福彩代銷者:增強責任意識 倡導理性購彩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慶人,這場活動需要您的參與!2024-09-04
- 積極參與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慶見義勇為”宣傳募捐活動倡議書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