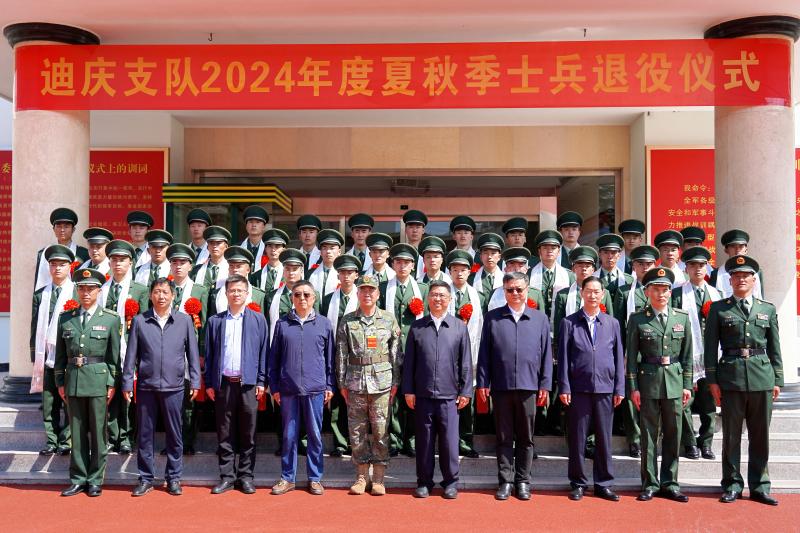|
一直以來,很難忘卻那朵去年秋末在金沙江畔的老家院墻下開放的牽牛花,那是一朵在秋陽下有些寂寞而認真地開放的極其美麗的花朵。 當秋風帶走小草的綠色,一棵粉紅的月季花逐漸接近白色的花瓣在秋風里舞動,池塘邊飛舞的蜻蜓歇息了它們透明的翅膀,蝴蝶的殘翅懸掛在灌木枝間的蜘蛛網上的時候,陽光里依然有一些溫暖的金黃,這一棵牽牛花從一棵低矮的黃果樹的枝葉縫中探出頭來,獨自迎著南走的太陽綻放著紫色的花瓣。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感動于牽牛花在一生的暮秋還那么認真地綻放著自己的美麗,在秋陽的溫暖里將美麗定格的勇氣和定力。 想起牽牛花,也讓我想起省城里的恩師言娳輝。那是一位慈祥得如同母親一樣的老師。在從教的歲月里,一直以來我都拿言老師作為自己的榜樣,反思自己是不是將自己的所有熱情、激情和愛心交給了自己的事業——醫學教育。也為自己后來的逃避與半途而廢感到深深的自責。 言老師是我在讀中專時教授病理解剖學的老師。二十多年過去了,言老師上課的儀態和內容依然在我的腦海里記憶猶新。也還記得她帶著我們一群醫學初學者到昆明穿心鼓樓她家那間低矮的房子里看病理征。 那是一個秋雨濛濛的日子,我們在課堂上學習了“巴彬斯基征”“克尼格氏征”“布魯斯基征”。作為初學者,我們很難從抽象的講解中理解神經系統受損后病人出現的那些臨床表現,而那時言老師家中有一個脊柱受損截癱的哥哥。聽說,她哥哥受傷之前言老師和她的愛人在甘肅蘭州工作,為了照顧病榻上的哥哥,言老師放棄了自己熟悉的崗位,回到昆明從頭創業。 在她哥哥的床旁,我們圍在四周,言老師拿著一根竹簽沿著他哥哥的腳掌邊沿滑動。“看,這就是‘巴彬斯基征,’這是‘克尼格氏征’,這是‘布魯斯基征’……”為了讓學生看得真切,言老師做得極其認真,而她的哥哥也是一臉耐心的表情。那時,我在想,作為一個病人,能那么坦然地接受學生的觀看,言老師發揮的作用一定不小。在后來的交談中得知,在言老師從事醫學教育過程中,他哥哥一直都為學生承擔了“教具”的角色。由此,我斷想,言老師是個坦誠的省城人,與她朝夕相處的人必然也都是坦誠的人。 真正對言老師的了解還是去年在秋天,那一天,我去省城學習并探訪言老師。二十年來疏于聯系,使我十分想念言老師。從工人新村到北市區,昆明與我彼此都很陌生。一路上我都在想言老師是不是老了,畢竟我自己也開始長皺紋和白發了,而且聽說老師還患了一次重病。 到樓下接我的是言老師的愛人裴叔叔,一個從空軍退下來的老人,也是個舉手投足和談笑間都洋溢著坦然和真誠的老人。隨著裴叔叔進門,戴著老花鏡的言老師從沙發上起身,雙腿有點顫。“小程,讓我看看你。哦,記起來了,樣子沒變,胖了一些。”我和言老師彼此緊握著雙手,看見老師有些衰老的模樣,我的眼角有些發潮。老師說,她是與死神抗爭活下來的人,如今她只剩下一側肺,肺心病一直纏身,但是她活得很充實、很滿足。 坐定之后,言老師從茶幾上拿起一本散發著墨香的書籍,那是她在病榻上就開始整理和撰寫的回憶錄《梅花香自苦寒來》。手捧恩師的書籍,那些字里行間記述的文字有一些是我熟悉的,一些是我聽過或者從其他的刊物上了解只字片語的,更多的是我這個年紀的人沒有經歷過的。我一邊翻看,一邊在想,老師是如何將1970年通海地震等事件寫得如此的詳實,每一個故事都是那么感人的呢。 我知道,我對老師身上的很多應該說是一個人的靈魂或者精神方面的內涵,的確是知之甚少。 牽著老師的手,她帶我參觀了她的珍藏室,我看到了老師對書籍、郵票、報紙的珍藏。這間小屋子是一個百科全書的珍藏地,一柜柜都是老師自己做的檔案,如剪報就包括了自然知識、動物、植物、人體、昆明的變遷等,老師說,她已堅持做剪報30多年。 30多年的堅持,一輩子的執著。我想,這就是老師這一輩子活得豐滿與坦蕩的原因。 在老師的著作里,我讀到了1990年11月8日《昆明日報》采寫的一篇通訊《流淌愛的紅燭——全國先進教師言娳輝二三事》。那個時候,離我畢業離開學校近半年,文章記載了很多言老師與學生間感人的事,也加深了我對老師“言娳輝對學生有真情”的理解。除了給予我的短暫教學外,言老師從教的每天、每堂課都給她的學生傾注了全部真情,難怪有那么多的學生在畢業離開學校多年后還會想起自己的老師來。 “快80歲了,我得珍惜自己的時間。”那一天,在交談中面對未來,我看見言老師的眼睛里是一種坦然與淡定。我看見在她的餐桌邊、茶幾上、床頭甚至衛生間里,都放著一個小本子和一支筆。老師說,隨著年紀的增長,記憶在下降,不管什么時候,想寫的詩句或者一些詞語想起來就得把它記下來,然后再慢慢整理。 讀著那些句子,我的心里有一些自責,我想起自己打發時間的方式,除了完成必要的工作外,大部分都用在和朋友打牌、電腦游戲和泡在一集又一集的情感劇里。自己的追求、理想、目標很多時候處于蒼白狀態。更多時候,做事總是有頭無尾,半途而廢。和老師坐在一起,自己倒是像個老人。經不住生活以及工作的磨礪,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甚至頹廢不前,這些都是我與言老師的最大差距。 告別言老師后,她的身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除了一遍遍讀老師的文章之外,一種崇敬在心底升騰。 當我看見老家的院墻外在秋風中開放的牽牛花時,我明白了,言老師不就是一朵在人生的季節里綻放的牽牛花么,她在屬于自己的季節和陽光下綻放美麗,將人生定格。(程志開) |
一朵在陽光下開放的牽牛花
來源:香格里拉網 作者: 發布時間:2012-02-20 18:40:02

頻道精選
- 2024 年迪慶州新聞系列綜合高級職稱定向評審通過人員名單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張衛東到迪慶交通運輸集團公司開展調研2024-09-05
- 福彩代銷者:增強責任意識 倡導理性購彩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慶人,這場活動需要您的參與!2024-09-04
- 積極參與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慶見義勇為”宣傳募捐活動倡議書2024-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