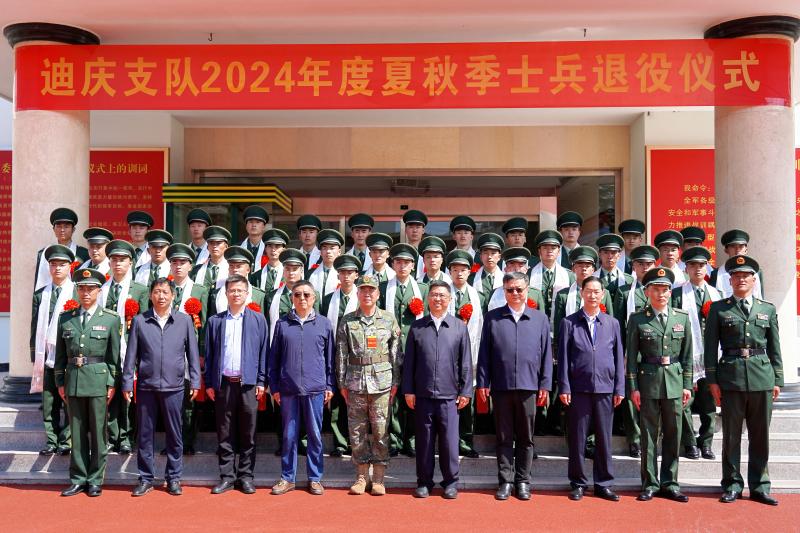|
秧小麥是家鄉的俚語,是俺娘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好多年之后,我理解了這句話的含義,它是父親入秋后最莊嚴、最神圣的一件事。 雞叫頭遍的時候,我無數次地被父親從夢鄉揪起來,他和娘到北坡種麥子,而我則要睡眼朦朧地起來淘米,做早飯。 時常,我都是極不情愿地從溫暖的被窩里鉆出來,生火做飯。也極憤怒自己早出生了幾年,不能像弟弟妹妹們那樣能安穩地睡到大天亮,而我則要一把把地把柴禾塞進灶膛,直到稀飯開鍋的那一刻…… 那些日子,定會是娘扛著鋤頭,牽著牛走在前頭,父親扛著耙,耙上一頭放著化肥,一頭放著小麥種子,走在后頭。他們很快就被夜幕淹沒。之后,我便會等他們凄婉悠揚的吆牛調,那一刻,我知道,他們的勞作真正開始了。 我深深知道,莊稼人的心中滿滿的,只有莊稼,莊稼是他們的生命和希望。播種、除草、施肥、收割都是神圣的,帶著崇敬和感恩,帶著汗水和喜悅。 我一直認為,父親是三鄉五里最老練的莊稼把式,他對莊稼總是拿出貼心貼肺的熱愛,幾十年癡心不變,把整個世界都給了莊稼,讓莊稼在心中生出七彩來。 麥種是父親親手培育的,揚場的時候,上揚頭那些顆粒飽滿的麥粒總會被他視如珍寶,早早地灌進麥包,那種小心翼翼的樣子,像是在呵護一位嬰兒,生怕驚擾了它們的睡夢。 翻地更是仔細,我們家里的田地總是比別人家多翻一道,父親也總是固執地認為土地乃萬物之源,好的土地才能長出好的莊稼。當別人收完麥子躲在蔭涼處沉浸在豐收喜悅之中時,他卻頂著烈日提前犁麥茬遍地的農田,還會乘濕抓緊時間耙平。夏天的日頭大,不大功夫土地就會干結,也耙不碎,即便是角角落落都不會放過。我們家耙過的田里都生出草來了,別家的麥田依然還是麥茬朝上,一片狼藉,那種不堪,讓人心煩。 秧小麥是鄉村最大的農事,父親會投入他一年中最大的感情。農家肥是他一車車拉進去的,一锨锨灑開的,那么勻,就像平均分配的。化肥、磷肥和鉀肥都要準確計算,不多也不少,多了,麥子會長倒;少了,麥子長不起來。 深秋的田野有些寒,他要乘著晨露把麥子灑進去,然后耙平,就需要早起,天不亮就下地。都說男耕女織,在我們家卻總是無法體現這一點,按娘的說法,父親秧小麥萬萬離不開她,牽牛、挖田角,打溝都離不開娘,我們總說父親,麥子有娘的味道,溫柔、綿軟,內心潔白。父親也會默認我們的說法,他會淡然地一笑了之,那份愛,心里、眼里都有。 村子里的人最佩服父親秧小麥的那份仔細,沒有用線牽,但麥田溝起得筆直,寬窄一致,既好看又實用。父親的眼睛就是線,只要他隨便在村子一轉,不用問,就可知道哪一塊麥地是我們家的,曾經好多次縣鄉檢查,父親的麥地都是作為樣板展示的。 一年一年,秧小麥會周而復始地輪回,而在黎明中勞作的父母會和悠遠的吆牛調一起,隨著晨霧慢慢縈繞心頭,總也揮之不去。(潘新日) |
秧小麥
來源:香格里拉網 作者: 發布時間:2018-01-03 09:54:03

頻道精選
- 2024 年迪慶州新聞系列綜合高級職稱定向評審通過人員名單公示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香格里拉景區直通車:便捷出行,一站直達美景2024-09-05
- 張衛東到迪慶交通運輸集團公司開展調研2024-09-05
- 福彩代銷者:增強責任意識 倡導理性購彩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下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中篇2024-09-04
- 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的用途及作用|上篇2024-09-04
- @迪慶人,這場活動需要您的參與!2024-09-04
- 積極參與2024年“99公益日·助力迪慶見義勇為”宣傳募捐活動倡議書2024-09-04